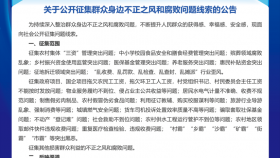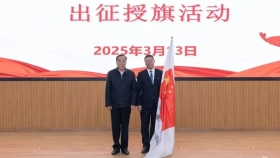【武汉战“疫”采访录】方舱医生张维森:折耳根护体,是我防护服上的名字
众望新闻讯(众望新闻记者 彭典 吴蔚) 时隔9年,32岁的张维森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武汉。
2011年以后再没有去过武汉的张维森是湖北恩施人。2月9日,带着贵州人民的嘱托,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(贵州)队员、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张维森前往武汉支援。
“武汉,我来了,我‘回家了’。”落地武汉后,他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2月10日,张维森进入武汉开发区体育中心方舱医院工作。2月22日,是张维森进入方舱医院的第12天。

张维森在武汉开发区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支援

这一夜,涌进400多名患者
出发前,张维森知道自己去的是方舱医院。
犹豫再三,他没有告诉父母去武汉的消息,父母看了他的朋友圈知道后,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嘱咐:“做好防护措施,注意安全,我们等你平安回家。”
“父母年纪大,不想让他们担心。”张维森解释道。
进方舱医院之前,院感专家组带领医护人员在酒店里学习操练防护措施和消毒流程,包括如何穿脱防护服,隔离消毒的流程等。

张维森在方舱医院内工作
张维森反复练习了一遍又一遍,就是要保证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,去救治更多的病人。
2月12日下午4点到晚上12点,这个时间段,400多名患者像潮水一样涌进方舱医院。院方特意在每一张病床上都配置厚铺盖和棉被,还加了电热毯。
张维森跟同事们一一核对患者床位信息、询问患者病史,给他们做体温测量、观察呼吸状况、测量血氧饱和度等检查,并引领他们去到自己的病床上。
这一晚,所有工作,都在忙碌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完成这些工作回到酒店已是凌晨1点,张维森早已没了睡意:“一下子来这么多患者,我也很紧张,生怕漏掉哪个环节。”
后来,方舱医院又陆续来了很多患者,现在已经有1000名左右。

患者的话,让人心疼又暖心
每天,进入方舱医院要走专门的通道,这趟4分钟路程,张维森走了很多遍。
初期,部分患者会比较焦虑,一遍遍追问:“医生,我的病严重吗?能不能治好?”
“你们都是轻症患者,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告诉医生,好好配合治疗,一定能早日出院。”张维森劝慰道。
实事上,方舱医院收治的是轻症患者,危险性相对较小。每天,医护人员会进行巡检,指导口服药。如果患者好转痊愈,经过检测可以出院,而一旦病情加重,则转至定点医院。

晚上12点,张维森下夜班后搭乘志愿者开的公交车回酒店
让张维森感动的是,他经常给患者检查时,患者会主动提醒:“小伙子,你离我远一点,我怕传染给你。”张维森说,这话听着让人既暖心又心疼。
一位50多岁患者的两位亲人因为新冠肺炎相继过世,连亲人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,患者哭红了双眼:“我担心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死掉。”
张维森很想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,却不能,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:“不要怕,我们都在!好好配合治疗,一定能康复出院。”

每天在群里报平安:我安好
进入方舱内要穿4层衣服,第一层是自己的内衣,第二层是手术衣,第三层是防护服,第四层是隔离衣。
穿上严丝合缝的防护服后,为了区分彼此,进舱的医生会在防护服上写名字。
张维森在自己的防护服上写道:“张维森,折耳根护体。”
“我想用‘折耳根护体’这样俏皮的字眼,能让患者感觉轻松一些。”张维森笑着说。
与患者相处久了,患者也时刻惦记着医护人员的安全。患者看到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出现小破损,都会第一时间提醒。“有时候,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。”张维森说。
防护服出现小的破损,医护人员会马上用胶带密封;如果是大的洞口,就需要立即更换。
在方舱这些天,每每有患者出院,是张维森最高兴地事情。
“张医生,等病好了,我要去献血。”张维森说,这是他来到武汉以后,听到最暖心的一句话。

张维森平日里热爱生活、热爱运动
张维森的好几个大学同学也都奋战在武汉“一线”,同学们“挤兑”他说,来武汉了,都不去找他们。
每天,张维森会在微信群里向大家报平安:
武汉第1天,我安好!
……
武汉第10天,我安好!
武汉第12天,我安好!
晚上12点,张维森上完夜班,搭乘志愿者开的公交车回酒店,望着车窗外的倒影,他告诉自己:“等疫情结束,一定去见武汉的同学,好好跟他们吃顿饭。”
扫一扫 手机端浏览